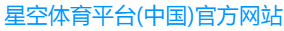提起魏晋南北朝,你想到的是什么?是“竹林七贤”的肆意酣畅、自在洒脱,还是《世说新语》中魏晋名士的清谈放诞、玄思机巧?是乐府长诗《孔雀东南飞》中的“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还是北朝民歌《木兰辞》中的“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事实上,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战乱频仍、民族融合的一段恢弘历史。公元四到五世纪,中国南北分裂。北方,五胡十六国铁马长槊,驱驰中原;南方,门阀士族动辄反目内战,血染长江。就在这各族争雄、战争扰攘的大时代,一位出身低微的南国将领,在一次次血战中崛起。
他的战绩谋略,在中国历史中罕有人堪匹敌,却少有人知晓,更未曾被演义为话本、传唱为戏文。只有辛弃疾一阕“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才能让人想起这位曾经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寄奴”刘裕……

新锐历史学者李硕,继畅销书《南北战争三百年》后又一精彩力作。以他一贯主张回到历史现场的细腻书写,侧重叙事,将原本一段冷门的历史,鲜活地端上读者书桌。通过一场场激烈的战事,以战史书写的方式,重新走进这个中国历史上承上启下关键时代。
李硕先生新书《楼船铁马刘寄奴》这本书以叙事见长,以坚实的军事、历史研究为基础,以近乎电影的细腻立体手法,对刘裕等东晋寒族武人的超凡战绩做了全景描述。活字文化编辑小闫读过后认为此书不论写法还是内容都实属难得,撰文与大家分享东晋历史的缘由始末、刘裕为代表寒族军人在东晋时代的作用,以此呈现东晋在名士风流、挥麈谈玄之外的另一种金戈铁马的面貌,更见刘裕这个人物的重性。
世界历史上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之间的交往,进行着和平的、有时是暴力的交往,间或以战争形式进行。战争对于人类历史的影响,除固有的破坏性之外,首先是用暴力打破了各地之间的孤立状态,是各地区各民族“闭塞状态的重大突破”,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交往的增多。
从公元前第 2 千纪中叶起,迄公元 13 世纪,游牧世界各部族先后对农耕世界掀起了三次历时长久的移徙和冲击浪潮。第二次浪潮始于公元2 、3世纪,直到7世纪。最早发动的主要是匈奴人、突厥人,后来还有进入黄河流域的鲜卑和拓跋诸部,进入波斯和印度的嚈哒,星空体育网址在匈奴压力下冲入罗马帝国的日耳曼各族以及稍后的斯拉夫各族。第二次冲击浪潮导致亚欧大陆两大高度发达的古典文明中心:罗马帝国与汉晋帝国相继瓦解。但罗马帝国与汉晋帝国的瓦解形成了殊为不同局面。欧洲全部蛮族化,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失去了独立发展的载体,只能作为底色深入基督教文化中,以待近代之复兴。
而中国则不同,因衣冠士族拥戴晋室立足于江左,自成独立政权,保有汉魏文化为正统的华夏文化源流,统绪不坠,传至齐梁,后与元魏北齐所保存之汉魏旧制、北周所代表之鲜卑野俗,虽互有岛夷、索虏之讥,而终归于相互激荡,逐步混合集结。在新的大一统局面下,新与旧密切结合,汉与胡杂糅混同,产生开放恢弘之隋唐盛世。中国文明底蕴深厚之旧文化,由六朝衰世转而因注入北方民族质朴基因(“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 , 新机重启 , 扩大恢张 , 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实为世界文明史上大可研究者”——陈寅恪《李唐氏族推测之后记》),获得新生命力,产生文质结合、胡天汉月、万国衣冠的李唐盛世。此种与欧洲不同的局面,如何产生,又赖谁人之力而得以维持,不得不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
陈寅恪治中国史,最重视三至九世纪中古部分,自称“一生为不古不今之学”,因为这一时代为中国史上中外文明、东西文化、南北族群频繁交流激荡的时代,与近代中国的处境,有相似之处。佛教之西来,即是改变中国思想的最重要文化事件。隋之平江左,出身胡汉混合之关陇贵族的杨广因醉心仰慕江南梁陈文化而大举提拔江南士人(科举的目的之一),进而久驻江都,不惜边缘化关陇旧将,引起南人北人集团矛盾激化,自己因此见弑于关陇集团将领宇文化及。可见,汉晋帝国崩解而成南北朝百年对立的最终结局,政治上是南入于北,文化上却是北入于南。此前辈学者论列已多,不需赘述。
陈寅恪做《述东晋王导之功业》,指出王导在元帝南渡之初,人心未附之时,笼络联合吴姓大族,使得后者抛弃胜国遗民的心理,允许晋室立足江左,与之一起拥戴王室,造就东晋南朝数百年偏安之局面,使神州免于全部陆沉,此所谓王导之功业。(陈寅恪:“当永嘉之世,九州空荒,但仅存江南吴土尚得称康平丰盛者,是谁之力欤?”)
王导既没,庾谢诸族,同心翼戴王室,破苻坚于淮上,保持江左衣冠文物不坠。但王导之政“宁使网漏吞舟”、“政务宽恕,事从简易”,与汉高帝“除秦苛暴,与民约法三章耳”以结纳秦民之心,以为己所用,用意正复相同。此等政策,施行于永嘉乱离之际,江左政权初建之时,用以调和掩盖北来士族与吴姓大族的矛盾,能收一时之效。因此谢安承之,“镇之以和静”。
但南北士族门阀之间、北来士族门阀之间矛盾始终不能解决,各大族之间制约与平衡成为东晋政局的特点,这种情况是导致恢复中原的努力始终不能成功的原因之一。“夫当时北方之士大夫,虽云不足与有为,然南方剽悍之气,固未尝减。使晋室东渡之后,得如周瑜、鲁肃、吕蒙、陆逊者而用之,北方之恢复,曾何足计?北方之名门巨族,挟一王室之名以来,自非其所能抗,而南方之政权,遂尽入北来诸族之手,何其能淑,,载胥及溺焉。直至北府兵起,江、淮剽悍之气始有所藉以自见,然积弱之势既成,狙诈之习未改,日莫途远,虽绝世英雄如宋武帝,亦不能竟恢复之绪矣。”(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更何况王导、谢安纵容豪强枉法蠹民,抑制寒贱利益,根本就是一种“牺牲人民,收买士族”(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的反动政策。
士族门阀以其阶级属性而论,洛京倾覆而相率其族人南渡,只为保家全身之计,“内乱不与,外患不辟”之义,于我何加?江南大片空旷土地供其垦殖,虽有筚路蓝缕之劳,但士族门阀借助政治特权,移家复业,广招徒附,又有世外桃源之乐,何必“克复神州”?“夫既徒为保家全身之计,则苟得沃土,自必如大月氏之西徙,志安乐而无复报胡之心。东晋之名流,率图苟安而怠恢复。”(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因此,王谢门阀虽有汉高帝笼络胜国遗民的现实主义谋略,却绝没有汉高帝统帅由秦国旧军队改编起来的汉军东出函谷关与项羽争雄天下之决心。
历史学者李开元教授认为在垓下之战追击项羽的五位汉军骑士,皆出自兵马俑的原型——秦帝国京师军。刘邦集团中,吸纳收编了大量秦帝国旧军人。由活字文化策划出版的《秦谜:重新发现秦始皇(插图增订版)》一书,结合考古发现,用历史推理的书写方式,拨开因为旧史阙文、记载失误、有意隐讳等原因而导致的层层疑云,重现风云诡谲的秦始皇时代,对我们熟悉却又陌生的始皇帝出身、末代楚王昌平君、秦楚关系、扶苏之死、焚书坑儒、秦末王嬴婴等历史人物事件做了新解读。全新重磅升级:新增李开元教授《解构“史记•秦始皇本纪”——重新书写秦始皇的历史》一文;收录大量精美文物、古迹插图,还原历史现场。
江左立国,初赖士族门阀之力,所谓“东晋门阀政治”,而门阀与皇帝共天下的局面,是一时形势造就(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东晋之末,门阀迅速衰朽,“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学士辈不堪经国,唯大读书耳。经国,一刘系宗足矣。沈约、王融数百人,于事何用”,此等风流名士,绝不敢委之国政,但东晋南朝,维系“衣冠上国”“华夏正朔”之名达数百年,江左政权保存的汉魏旧文化得以独立发展,除偶然因素导致的侯景之乱外,未遭严重破坏,更未像罗马古典文化一样灭亡,影响所及:一则刺激北方游牧诸民族政权在争夺华夏正统的动机下主动汉化(比如后魏孝文帝之迁洛、宇文泰以“周官”立国),二则以待统一国家重建之时,成为新时代盛世的重要元素,其赖谁人之力欤?
民族大迁徙造成的动乱之世,造就了另一个与士族门阀实力相当的强大社会集团——流民集团。刘渊石勒占据中州,除衣冠士族避乱江左之外,还出现了大批以宗族乡党相结聚的流民相继南下,这些人的领袖大多是一些门第阀阅不高的豪强地主,即“流民帅”,著名的比如郗鉴、祖逖等。流民集团为了自保不断与游牧民族作战,保持着强固的组织性,且“人多劲悍”,其实是一种军事组织,郗鉴、祖逖或者将略不凡,或者魅力出众,其实是军事组织的领袖。来自青州、徐州的流民集中于江淮地区,来自雍州、司州的流民大多集中在襄汉地区。晋皇帝和士族门阀们看重他们的军事实力而对他们笼络任用,加以官职,但又对他们充满猜忌,不允许他们过江,而迫使其成为抵御游牧民族南下进攻江左的屏障。流民帅大多以豪杰之气著称,比如祖逖中流击楫的典故,他们虽非彻底质鄙无文,要之不能操弄玄谈名理,因此与衣冠士族们界限分明,不能处居朝堂之上,只能远驻江湖之间,捍卫江淮防线。江左政权的保全,天然有他们的一份功劳。
“晋主虽有南面之尊,无总御之实。宰辅执政,政出多门;权去公家,遂成习俗”(《晋书·姚兴载记》)的门阀政治局面下,皇帝与门阀、门阀之间处于不稳定的冲突与制衡中,“流民帅”成为各方争相拉拢的“第三势力”。京口地区流民云集,郗鉴在此经营多年,整合盘踞在此地的流民势力,京口重镇初具规模,连桓温也不得不承认“京口酒可饮,箕可用,兵可使”。谢安执政后,为了与盘踞上游荆州的军阀桓氏相对抗,派遣谢玄担任徐(治京口)、兖(治广陵)二州刺史,因郗鉴之旧,更“多募劲勇”,正式组建“百战百胜”、“敌人畏之”的北府兵。之后便是东晋乃至中国史上广为人知的淝水之战的故事。后司马道子专权,谢安隐退,寒族出身的武人刘牢之在桓楚篡晋的风波中,投降桓玄身死,一位不世出的军事奇才寒族将领刘裕登上舞台,重新组合了北府兵这个军事集团。
一部《世说新语》,多载名士隽永清谈,比如“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世说新语·任诞》)之语,被认为是魏晋名士任情放诞的典型,此种名士风范,堪称魏晋文化的象征。以至于“名士”“玄谈”“自然”成为定义魏晋时代的标配。玄学一改支离破碎、繁芜衍漫的经学风气,离经言理,要言不烦,开创得意而忘言的风气,对中国思想是一次改造,之后的宋明理学亦暗中传承它的内核。但玄谈作为一种人生取向乃至士大夫风气,多遭到古今史论者讥议,并非值得夸耀的时代精神。“其识解自较汉人为高,然其所规画,或失之迂阔而不能行;甚或视世事大渺小;谓有为之法,终如梦幻泡景而不足为。其力薄才弱者,则徒为自娱或自全之计,遂至新亭燕集,徒为楚囚之对泣焉。”“此晋、南北朝之士大夫,所以终莫能振起也。”(吕思勉)
哥大教授商伟所编选的《给孩子的古文》中,从《世说新语》中选了十则文段。此选本精选从先秦到近代的古文八十篇,内容既有诸子百家之言,如《老子》《庄子》等篇章,也有史传篇目;既有脍炙人口的唐宋八大家散文,也有历代学者名家的精彩论断。书中古文言简意丰,有古人充满哲理的对话记录、朋友间寄思怀远的感情抒发,有古代名家对历史、人生、艺术的思考感悟,还有长辈的谆谆教诲,篇幅长短不一,读来朗朗上口,有助于从小培养古典文学素养。
顾炎武著名的《日知录·正始》更是批评士族醉心玄谈清议之风,以至于礼法大坏,“乃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胡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咎哉!”,他主要是从传统“名教”角度出发批评玄学思想对政治的瓦解作用:“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虽说不能以“末流之弊”,责备“创始之人”,但士族在政治危机不断的魏晋时代寄心于老庄有无之辨、玄远之谈,确是缺乏责任担当的表现。但这段激扬文字更是广为人知。
宋武帝率北府诸将,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克复两京,侵斩敌酋,虽“不能竟恢复之绪”,但其事迹不可磨灭者有二:宋武帝连年征战,以赫赫战功代晋自立,开创的由寒族将领集团相继代立的南朝。史称刘宋一代“主威独运,官置百司,权不外假”,已经恢复中央集权。衣冠士族虽然保有文化上的巨大影响力(连鄙陋如侯景也知道向江左高门求取婚姻),但仅以清要之职养尊处优,不与政事,成为彻底的寄生于皇权之下的百足之虫。建康附近的士族门阀,几乎覆灭于侯景乱梁之际。
“起自布衣”(宋武帝)、“布衣素族”(齐高帝)、“其本甚微”(陈武帝)的军阀皇帝联合寒人,循名责实,纲纪庶务,重建专制政治,保存江左华夏文化,其功业不亚于王谢诸族;宋武帝刘裕“当神州陆沉之余”,“宁无痛愤而思奋起者?”,以步卒而屡挫北族拓跋、慕容诸部劲骑,使得游牧民族机动性优势不得发挥。
古来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作战常常处于下风,读史者皆有感触。汉武帝继文景二代,峙中国之大,虚耗海内之半,举全国之力,击破匈奴,最后国家疲敝,不得不下轮台之诏,自愧“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事。”如宋武帝者,仅据江左荒蛮之地,率流民武装,内有门阀掣肘,外有横行中原的塞北诸族,仍能一鼓作气连战连克,若非王镇恶和沈田子自乱关中,导致精锐损失殆尽,失去关中犄角之势,打断了他北上讨伐拓跋魏的计划,造就什么样的形势,还未可知。
在世界历史上游牧世界各部族先后对农耕世界第二次浪潮的大背景下,亚欧大陆西端的西罗马帝国不能抵挡匈人王阿提拉之兵锋、日耳曼蛮族之凭陵,日耳曼人各族的统治随之建立,东罗马皇帝瓦伦斯亦战死于阿德里亚堡之战,版图缩小到巴尔干地区。而亚欧大陆的东端的刘裕,还能依靠非凡武略几乎克复神州,扭转乾坤,仅从军事角度,就足称当“绝世英雄”之名。
无怪乎生于南宋之末的王应麟对东晋北伐功业,赞美不已。王应麟曰:“焚石勒之币,江左君臣之志壮矣。僭号之国十六,而晋败其一(原注:苻坚),灭其三(原注:李势、慕容超、姚泓)。不可以清谈议晋。”(《困学纪闻》卷一三)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亦承袭其说:“东晋君臣虽偏安江左,犹能卓然自立,不与刘、石通使。旧京虽失,旋亦收复。视南宋之称臣称侄,恬不为耻者,相去霄壤矣。讵可以清谈轻之哉!”(“不与刘、石通使”,田余庆教授别有论说,认为是八王之乱司马越司马颖矛盾的延续,详见《释“王与马共天下”》一文。)
东晋对北族政权的态度,固非全部是气节使然,但相比于赵宋南渡君臣,高下之别,不难判断,无怪乎王应麟读史而“自伤本朝”(阎若璩注),对清谈误国之说完全不屑。桓温、刘裕的北伐功业,贯穿东晋王朝的始终,洛阳、长安也在东晋和北族政权之间几度易手。
这是魏晋时代在风流名士、玄谈清议之外的另一种面貌。让人知道,在名士风流的魏晋之外,还有一个金戈铁马的魏晋。笔者虽读史日浅,于此金戈铁马之魏晋,却不由感慨系之,因此甘冒效颦之讥,称之为“东晋刘裕之功业”。而这个魏晋,长期被人忽略,大概是玄学在学术史上影响非常长远,彻底改造了中国思想。名士清议,又堪为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满足古往今来不少人的情怀。寒族武人之功业,却如其他六朝旧事文物,付诸故国空城、故垒萧萧,台城烟柳,碧草连空,不仅凭吊乏人,更没有像汉末曹刘孙诸位英雄那样被演义为经典,且当今找不到一部影视剧像《汉武大帝》那样的影视剧为他们作词立传,被吕思勉赞誉为“绝世英雄”的宋武帝刘裕成了仅在中学语文教科书辛弃疾那篇词下注释出的,鲜为人知的历史人物。
曾以《南北战争三百年》《孔子大历史》惊艳世人的李硕先生有感宋武帝事迹湮没不彰,结合最新军事历史研究成果,写成这本《楼船铁马刘寄奴:南北朝启幕战史》,重叙事而非考据,重述刘裕与北府兵集团诸将领东征(孙恩卢循)北战(慕容拓跋)的详细过程。
作者自言宋武帝刘裕与罗马帝国军事领袖尤里乌斯·凯撒很类似,皆属富于将略,“制人而不制于人”之善战者,又以超凡魅力形成团结在自己周围的军人士兵集团,以为后盾,移贵族(门阀)国祚。凯撒自述戎马生涯,《高卢战记》《内战记》广为流传,宋武帝未遑于此,深为憾事。实在是绝妙的类比。作者又感叹刘裕之武功,不被文学演义所流传,在本书中,除去运筹部署的战略得失分析之外,更以风起云涌、跌宕起伏的文学笔法还原了人仰马啸、草木皆兵的战争历史场景。东晋一代人物,名士风流与金戈铁马兼备,何逊于三国?这本《楼船铁马刘寄奴》,可为读者呈现一部精彩不下《三国演义》,可靠性不下《高卢战记》的军事历史作品。
在历代的王侯将相当中,刘裕的声望和影响并不十分突出,但他的战绩谋略,在中国历史中却罕有人与其匹敌——他出身低微,凭实力在一次次血战中崛起,两个北方政权、两个江南王朝、若干割据势力,先后覆亡在他脚下;他终结了江南士族百年共和政治,建立起血腥、高效的军人政权——而且从战争的紧张程度、从实力与战绩的“相对值”来看,刘裕战史的精彩度,不亚于横扫亚欧大陆的成吉思汗。
本书作者以细腻的文笔,书写了刘裕一生跌宕传奇的战争生涯,同时在写法上进行了若干有意识的探索,对此作者也十分有信心,在后记中放话说:“写出这本战史也有点‘打擂台’的意思,期待能出现和本书较量的战史作品,我们的历史研究和叙事也要进化。”
李硕,北京大学中文系学士,清华大学历史系硕士、博士,现供职于新疆大学。从事中国古代历史、边疆民族问题研究。著有《南北战争三百年》《从大漠绿洲到玉石山谷》《孔子大历史》等。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